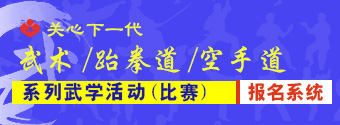-
 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八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八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
 2025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七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2025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七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
 2025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六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2025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六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
 2025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五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2025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五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 1《中华幼儿武术》 教材内容及订购方式
- 2让孩子学习武术 早已超越了学一个特长的范畴!
- 3让武术成为孩子的特长
- 4中国武术段位制
- 5中国武术段位制晋段标准
- 6民国武术国考揭秘中国武术实战能力
- 7传统武术实战的核心——根劲、整劲 和身法
- 8传统武术的实战运用
- 9这才是中国实战武术
- 10武术知识拓展之大成拳

近日,“格斗狂人”徐晓冬KO“太极宗师”雷公事件,引发了诸多有关中国武术的争论。其实,在历史上,中国武术曾多次亮相擂台,并留下不少可信的文字、照片,以及视频记录。仔细研究这些记录,是不难管中窥豹,得见中国武术之真实战力的。
近代以来,中国武术有据可查的几次擂台实战,都是笑柄
1、民国两届“国术国考”,主流技术是搂抱滚地、咬脸、对着抡、互相戳
对于中国武术在擂台上的表现,古书中的记载或语焉不详,或缺少可信证据,大多属于传说性质。直到近代,随着大众媒体的出现,我们才有机会见到真实武术对决的样子。比如中华国术馆组织两次“国术国考”的情况,即被媒体记录了下来。
1928年10月,第一届国术国考在南京举行,参加选手有400多名。考试分为预试和正试两部分,预试为个人表演赛,评分及格者,方能参加正试。正试中,选手通过抽签分组,再进行淘汰赛。只要手、肘、脚等部位碰到对方,即可得“一点”,“三点二胜”;或直接击倒对方,也为胜利。当时《申报》对此进行了连续报道,如比赛第三日,出现选手“孟唐春失败不服,猛咬与赛者之面,鲜血淋漓”的场面。在这次国考中,很多时候,都是两名选手缠斗许久,甚至出现搂抱滚地的局面,观众们对武术的浪漫化想象完全被打破。
1933年10月,第二届国术国考在规则上更加科学化,选手按体重分为五组,并规定使用拳套。时人田镇峰撰文说,“在短兵比赛时,我注意留心的看了几天,真精彩的,能施展出技术来的,可以说是没有。长兵比赛时,倒是有几位能施展出枪的能力。拳术比赛的成绩,更是糟而且糟了。摔角比赛,还不如日本的柔道”“在短兵决赛的时候,人人手里拿着一支‘哭丧棒’式的短棍,两人上了台,不是对着抡,便是互相戳,其外就是拼。决赛应当精彩,精彩就是这样!”这样的中国武术,当然并不好看,让人大失所望。
2、1954年,太极拳、白鹤拳两大名家对决,与乡野村夫打野架并无多少区别
至今为止,传播影响最广的一次中国武术擂台赛,是1954年澳门的“吴陈比武”——太极拳宗师吴公仪和白鹤拳名家陈克夫公开交手。这是太极拳史上,第一次有确凿文字记录,且有照片、视频为证的比武。陈克夫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双方在第一回合先是互探虚实,互有攻守,但都没有激烈的攻势。但当第二回合钟声响起后,大家开始抢攻”。
当年香港《大公报》对此次比武的报道,写得非常热闹。比如,关于比赛第二回合,报纸写道:
“陈克夫突然用一记‘撩阴槌’,自下而上猛烈地向吴公仪‘撩’去。吴公仪把腰一弯,上身向前伸展,但仍然被陈克夫的‘撩阴槌’击中小肚。紧接着,吴公仪一个‘七星槌’,趁〇肚缩、上身伸展的机会,右手一拳正中陈克夫的鼻梁,陈克夫的鼻子当场再次出血,流得满裳都是。台下叫声四起。”
3、中国“国术”多次远征泰国,一再惨败于“泰拳”
中国武术也曾在擂台上,公开和外国拳术有过较量,如香港“国术拳手”几度对阵泰拳拳师。
(1)1958年,香港太极拳师40秒被泰拳拳手击昏
1958年,香港著名太极拳师胡胜、张耀强接受泰国侨团邀请,征战泰国。比赛时,“首战开始后不足两分钟,张耀强一轮快攻,以太极手法扭倒泰将沙原塞,旋即被对方一肘击中胸部,倒地败北。继而是练太极十五年的胡胜,出场时仅四十秒,即被泰拳师巴越借围绳反弹力,一记右肘拳中太阳穴,顿扑地昏倒。”张、胡二人回香港后,自称是“错饮赛场一杯水,至神意不清”,才导致失败。香港武术界对此愤愤不平。
2)1974年,中国“功夫拳”在泰国全军覆没
1973年12月,香港拳手翟光和邝汉杰也在泰国迎战泰拳拳师。比赛现场,“一经交手不及分钟”,翟光“被泰拳师玛纳勒飞腿踢中太阳穴,倒地不起”“其同伴邝汉杰亦不堪一击,依样在半居之内,遭对手碰诗里毛腿踢倒,不省人事”。对于此次失败,香港方面对公众解释说,“一是仓猝成军,未经充分准备;二则是不习惯穿手套,令其功夫绝招无从发挥,比赛时吃亏”。
随后,香港国术界组织人马“复仇”。
1974年1月,香港拳手区辉带徒弟到达泰国,并在赛前达成协议,允许他们赤手空拳,以便于发挥中国功夫的绝招。对此,香港《工商日报》报道,“数名香港中国武术师傅将于一月二十二日在泰国与一批泰国拳师进行四场生死决斗之比赛。双方经理人于星期三在此间签署一份生死合约,他们并且扬言能够将对方之选手击毙”。在实际比赛中,泰国方面虽然只出动了二流选手,还是连赢香港选手五场。香港拳手在这几场比赛中,都是“一触即溃,无一能战足一局,支持最久者亦仅两分二十秒,最短者二十秒”,以至被失望的华侨指为“豆腐拳师”。泰国媒体则称,“这是功夫拳史上暗淡的日子”。
(3)香港“国术界”远较同期的大陆武术界重视实战技击,仍一直无法匹敌泰拳这类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格斗拳种
平心而论,相对于大陆自1949年以来废弃“实战技击”,而将“身体锻炼”作为传统武术的唯一发展目标,使武术全面套路化、体操化、杂耍化,香港传统武术界其实仍部分保持着对实战技击的追求。即便如此,自50年代以来,香港“国术界”在面对泰拳这类围绕着实战技击,依赖科学(而非玄学)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格斗拳种,也从未取得过任何值得夸口的战绩——前述两次全军覆没,并非香港“国术界”灰暗史的全部。比如,1961年5月,香港体坛名流韦基舜等人组织香港国术拳手与西洋拳手,赴柬埔寨金边与泰拳手比赛,结果亦是泰拳取得五胜一和的压倒性胜利。
4、80年代,大陆武术界能够与前来友好交流的泰拳手对垒者,乃是脱离了传统武术的散打选手
80年代,具备实战技击能力的“散手”再度被大陆纳入“武术”的范畴。1985年4月,香港、泰国武术联队来上海友好访问。与之在友谊赛中取得胜利的,正是武警出身的散打选手(比赛系按散打规则而非泰拳规则进行)。而在另一场由某“气功大师”、“绵拳高手”出场的交流赛中,“一开始绵拳高手即拼力猛进,三度扑攻,一度将泰将抬起掷于台上。未几遇(泰拳手)盛叻反击,中膝撞腿踢在台上环行回气。再战,其扑拳已失威胁。第二局泰将看准对手势已尽,全力反攻。局末绵拳高手胸项间中膝跪地,即闻完局钟鸣,双方按例被判打成平手,和气收场。”看似平局,实际上是吃了大亏。据说此战过后,“当时上海体协的内部结论是,我们是上了尤具意义的一课,此后散打发展必须全为推向擂台竞赛的实战道路。”(《坤青信箱》,《中华武术》2002年第7期、第10期)
实战案例早已证明:热衷于玩“套路”的中国武术,没有实战性
1、民国时期,国术界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中国武术重套路不重实练,没有战斗力
以上,乃是“中国功夫”在擂台实战中的可信案例。这些案早已证明:中国武术作为套路表演,招式设计繁复,很具有观赏性,但这些招式套路在实战中并无用处。中国拳师一旦走上擂台,就只能凭借本能乱打,被接受过系统格斗训练的对手轻易击败。
这个问题,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引起了国术界的注意。
比如:1934年,有人在《国术统一月刊》撰文,指出“西方拳术简单,不若国术变化多端,足以应付无穷”。文章认为,中国拳师“平时以练身之死套子,以应变化万端之比赛场合,临时无所措手足,势固难免”,而“西洋拳之训练,除初学进阶,必须击球、跳绳,以及专练发达肌肉运动外,则实习尚焉。实习以对搏,斯时在规则内,得各施所长,各尽其能,熟能生巧,其终极即能运用自如,其手法虽简,亦能变化万端”。
吴公仪和陈克夫在擂台上毫无章法的表现,即是该文所言及的日常极少进行对战训练的现象的一个明证。
再如:1935年,有人在《国术声》发表文章,讨论“国术与搏击”的问题。作者指出,要参加竞技性的国际比赛,必须学习搏击,“我国的拳术,是侧重于单人练,虽有二人对手,出拳起腿,都是配搭好的;且因前辈抱着各收秘密的缪见,将应用的方法,失传不少,所以不如搏击的硬干、实干收效的快!在普通一般为运动而运动的,则仅练习国术已够,不一定强之都练搏击,且于事实上也办不到;若是有志造成技击专家的,则非兼练搏击不可;预备参加国际拳斗比赛的,更不可不练习!”
香港拳手惨败于泰拳拳师,亦是该文所言及的日常缺少搏击训练这一现象的明证。
2、有趣的是,当代大陆武术界,曾长期坚持认为:中国武术的特色就是套路,而非用于实战,所以不需要技击性
比如:自幼学习武术,后来成为体育系教授的康绍远,在上世纪80年代和学生孔定胜提出了“技击不属于武术的范畴”这样的观点。戴国斌在撰写:《武术:身体的文化》一书时,专门去采访了康绍远。在康绍远看来,“武术就是套路,套路的形成才表明了武术的形成”“武术就是套路,没有套路还能叫武术吗?”
对于武术的实战性,康绍远阐释说,“武术表现了攻防形式,但是不能用。为什么说武术不能用呢?因为武术有姿势的要求,没有姿势要求也就不成其为武术了,而打人、打架需要什么姿势呀?”“拳击里的架打与武术架打不一样,武术架打有姿势要求,不是你站着这么打就完了的,你要是没有姿势,咱们则会说你武术不行。”同时,他还认为:“武术不是起源于技击,而是起源于舞蹈。不能因为动作跟技击好像类似、相同,就误认为武术是为了打人的技击性练习”。按照这种逻辑,武术不能成为一种搏击技术,也就顺理成章了;中国武术不能打,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学武出身的康绍远,对武术本质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年轻时,我也是坚信武术的技击性。后来接触了拳击、摔跤、击剑以后,从武术与这些项目的比较中,我才发现,武术就是一个锻炼项目和锻炼身体的各种姿势:如果不练习拳击、摔跤、击剑等项目,你是不会认清这个问题的。并且,从技击的角度来看,只练武术在认识上会走上歧路”。
康绍远的这种观点,当然不是个案。事实上,自50年代以来,大陆官方武术界即致力于对“唯技击论”的批判,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取消了对抗形式的武术比赛,将“套路”确定为武术的主要内容,以“武术表演”全面取代了实战搏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