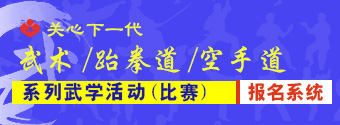-
 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八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八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
 2025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七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2025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七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
 2025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六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2025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六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
 2025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五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2025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第五竞赛日视频集锦视频 观看次数: 99+
- 1谈少年儿童武术基础训练
- 2武术对儿童竟然有那么多好处
- 3少儿武术训练方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
- 4儿童几岁可以练习武术?有什么好处?
- 5练习武术对少年儿童的三大益处
- 6小孩练武术有什么好处
- 7少儿训练武术的好处
- 8孩子4岁可以开始学武术,常练习可少生病!
- 9幼儿学习武术的好处有哪些
- 10浅谈少年儿童在进行武术套路训练中应注意的问题
王岗 张大志 苏州大学体育学院
1 中国武术“从‘体育’走向‘文化’”命题的理论诠释
这是一个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时代。因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因为,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因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化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在我们进入“十二五”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战略被提升到国家意志的平台之上。文化的价值被肯定,文化的力量被认可,文化的地位被提升,文化的魅力被彰显。因此,就传统文化而言,思考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厘清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挖掘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重塑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就应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基于此,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中国武术而言,从还原中国武术的文化真实出发,来实现中国武术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和文化使命,就成为一个崭新的研究命题。
对于提出“中国武术从‘体育’走向‘文化’”的命题判断而言,从当下学界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武术”、“体育”、“文化”的认知水平出发,在以“文化”、“体育”、“中国武术”三者之间是一种完全递减式的隶属关系作为判断标准的情况下,更多的人们则会指出这一命题无疑是一个“伪命题”的论断。因为,在国人心中,“中国武术”、“体育”、“文化”三者之间这样的关系分层已经成为学术界对中国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并且这种研究的立场和出发点已经根深蒂固。即:中国武术是体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正是基于大多数人对这一命题的质疑,才有了对这一命题的合理性、科学性进行理论诠释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体育”一词是由日本人创造出来的。对于我们接受和应用“体育”这一词汇的时间来讲,应该说只有100年左右的历史。然而,正是在这10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对“体育”一词的使用和意义开发就达到了极致。“体育”几乎成为了所有“身体运动”的代名词。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具有“身体运动”特征的中国武术被无情地“安置“在了所谓的“体育”之中。之后的几十年,“中国武术”就被贴上了“体育”的标签,成为体育学、体育教育、体育运动中的一部分内容和一个具体项目。进而成就了“武术就是体育”的不完整认知,甚至是错误的认知。
导致这一错误分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核心的问题应该说是来自我们对“体育”和“中国武术”二者原点问题研究的肤浅。百年来,尽管行政主管部门和广大学者也试图对“体育”、“中国武术”概念进行更为科学、准确的研究和解释,但非常遗憾地是,我们始终没有给出“体育”和“中国武术”一个统一的、具有说服力的科学概念。
因为,在界定“体育”时,我们常常都摆脱不了异域的坐标;因为,在更多人的心智中“体育”就是“运动”,“运动”就是“竞技”,体育就是舶来品。什么是“体育”这个问题,就成为体育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出现了,“体育”是体育工作者最常用但又不容易搞清楚的一个概念。进而导致了我们对“体育”的曲解、误读。我国最具权威的研究生教学用书《体育原理》中明确指出:“由于各国对有关体育概念有不同的解释,字面上也不相同,当我们从日本、美国、苏联等不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历史时期引进‘体育’与体育有关的概念,而又将他们统统译成‘体育’之后,导致了我国体育概念比其它国家更加混乱的显现,这使得我国体育概念的问题就更多了”[1]。
对于“体育”概念长期的、不确定的理解和表达,导致了我们对“体育”本质之所在的五花八门的理解。并在这个五花八门的理解之中,不断地选择阶段性“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也就形成了我国体育发展战略的功利性目标设置,如: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等。进而导致了在以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占绝对优势环境下的“中国武术”在“体育”中发展的举步维艰。
固然,中国武术具有鲜明的体育特征,也具有体育运动所表现出的基本特点,但完全将其归划在“体育”范畴的做法,显然是经不住最浅显的推敲分析[2]305。正如,已故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先生和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先生指出的“我们现在开展的项目有40多个,但武术不是四十分之一,它应是二分之一”,“武术是体育又是文化,具有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武术属于体育,但高于体育”等科学论断那样,我们仅仅将中国武术置放在体育概念、范畴之下,来开展研究和寻求发展之路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不全面和不科学的。
基于此,本文提出的“从‘体育’走向‘文化’的中国武术”研究命题,就不应该是一个所谓的“伪命题”。
将中国武术研究和发展路径的设计,从“体育学”领域延伸到“文化学”的领域;从“体育”领域延伸到“文化”领域;从“体育武术”领域延伸到“文化武术”领域,就应该成为中国武术发展必须建立的新理念。
2 中国武术在“泛西方化”思潮下的体育化之路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所谓“夏夷之分”,而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文化源流之间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关系模式,这就是“以夏变夷”,即以华夏的文化来改造、同化蛮夷的文化。“这种‘以夏变夷’的基本模式,导致了中国文化形态的超稳定结构,培养了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3]3。并在我们民族的心智中,长期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异质文化的能力。但自1840年起,“在铁与血的耻辱中猛然醒来的中国人发现,一直自视为天下中央的‘天朝大国’不过是世界的一角,而且较之那些遥远的‘异邦’远远地落后了。”[4]自此,中华文化强大的同化异质文化的能力再也没有得到发挥。此后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一直在走一条“以西变中”、“以西化中”的文化改良之路。对于这一结果,历史学家早就指出:“18世纪以后的世界历史,就是西方怎样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因此我常常也把这段历史称为‘泛西方化’时代”[3]270-275。正是这种“泛西方化”时代的出现,使得中华文化走进了一个“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以西变中”的时代。
具有典型文化意义的中国武术,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走进了“以西变中”、“以体变武”、“以奥变武”的发展场域。
中国武术的“以西变中”、“以体变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谭华先生指出的“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人士蜂拥而至。中国人以新奇而蔑视的态度注视着随他们出现的西方体育活动。随着新军编练规模的扩大和新学的发展,西方体育活动逐渐与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发生了联系,西方体育观念与中国人头脑中固有观念之间的冲突随之而生,并且日益尖锐和扩大”[5]那样,包括中国武术在内的民族传统身体文化的“以西变中”和所有的传统中华文化的西化一样,也经历了国人对西方体育“不屑一顾”的蔑视,也经历了国人试图证明一切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找寻。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其最终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能占到上风。新学制体育的实施和武术成为学校体育必修科表明双双都有所发展。但随着人们对西方体育的不断接受,“洋体育”派大多数承认了传统体育的价值,但同时也极力强调对传统体育必须进行整理和改造。由此,拉开了“以西变中”和“以体变武”的中国武术的体育化之路的大幕。
“中华新武术”的产生,就是中国武术西方体育化的最初成果[6]。这种新的武术方式的出现和逐步地被推广和认可,其本身就是“以西变中”、“以体变武”的结果表现。包括后来的“中央国术馆”的课程设置,甚至是霍元甲所创建的“精武体育会”所传授的内容,无不折射着“以西变中”、“以体变武”的传统中国武术改良的印记。可以这样说[7]30-39:中国武术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就被大量地融进了西方体育的思想,已经开始了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化的融合之路。
中国武术完全的“以体变武”,应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的体育事业是沿用着前苏联的发展模式,也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在我国的体育组织机构的设置、开展项目的选择上的近乎全面的西方化。1957年,国家体育主管部门从西方体育运动简单化、规范化的角度出发,组织了体育界、武术界专家,研究创编出了面向不同层次人群习练的22个武术拳械套路。这些拳械套路的出现,应该说是传统中国武术被体育化的一次彻底的洗心革面的改良,是西方体育影响改良武术发展的最为显著成就。之后的1959年制定出台的《武术竞赛规则》,更是彻头彻尾的“以体变武”的产物。它所涉猎的裁判细则、组织机构、项目分类都雷同于现代竞技体育(体操)的规则。
这次中国武术的被体育化改革,其核心的指向就是完成中国武术的体育化角色定位。之后的几十年,中国武术就理所当然地按照“体育”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开始了真正“以体变武”的“西方体育化”发展。建立在西方体育价值体系中的新的中国武术发展,一方面成就了“以增强人民体质为宗旨的健身武术”的快速发展,“武术成为增强人民体质的方法和手段”成为了发展中国武术主题之一;其二,在举国体制和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指导下,形成了“以提高套路运动技术水平为主的竞技武术”的强化发展之路;其三,实现了“武术走进各级各类学校‘体育课’和‘体育学院’的正规教育体制之中”的教育地位的提升。等等这些举措和成就的取得,其核心主旨是建构了一个新的中国武术认知定位[7]41-49,即:“武术是体育锻炼的方法和手段”、“武术是竞技体育运动的一个项目”,“武术是体育课中的一个内容”,“武术是体育学院的一个专业”,以至于后来确立的“武术学科是体育学科下的二级子学科”。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忌讳地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武术发展最显著的成就,应该是实现了传统中国武术的“被”体育化。
今天的中国武术已经完成了“以体变武”的文化同化目的。并且,“以体变武”后的新的中国武术形态———现代武术、体育武术,历史地占据了中国武术发展的主战场。与之相反的则是传统中国武术开始从历史的长河中渐渐地退出,成为中国武术发展中的配角。
中国武术在实现了“武术属于体育”,“武术就是体育”的“以体变武”之后,“以奥变武”的中国武术发展的信念就越来越强烈。因为,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青睐由来已久,在多数人的心灵深处,在奥运会中获得奖牌早已成为中国体育发展的最高追求。正是基于中国政府和民众的这种心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体育发展从一开始就走进了一个奥运项目极大化、主体化、快速化的体育事业发展时期。
从1979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之后,中国武术在中国体育事业中的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在1982年的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开展国际交流,积极稳步地向国外推广”的武术发展方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之后的30多年里,我们不断地用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的理论、方法,对“以体变武”之后的中国武术实施着“奥运项目化”的改良。甚至,时至今日,我们还在期待着这一目标的实现。
“以奥变武”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84年。学者们“自1984年筹备成立由中国牵头的国际武术组织起,把武术推向世界的目标中已经蕴含着进军奥运会的决心”的评价就可见一斑。围绕着这一目标,20世纪90年代之后,更是加快了“以奥变武”的目标追求。从1994年、1996年和2000年的《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修改,以及全国武术训练工作会议围绕着武术套路技术发展,所提出的追求“高、难、美、新”的发展方向,就不难看出我们“以奥变武”的决心和信心。正所谓,“在吸取体操、艺术体操、跳水、花样游泳等现代竞技体育项目的评分方法的基础上,加强量化指标,提高区分度和准确性,采用切块打分,制定出指定动作和难度创新动作的质量,并鼓励创新,进而促进武术套路技术水平继续向‘高、难、美、新’的方向发展”[8]43。
“以奥变武”的加速实施和推进,应该是与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的时间是相对应和吻合的。2001年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就开始了依据《奥林匹克宪章》,筹划并选择启动了武术进入奥运会的行动。第9届全运会之后,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就明确指出:“武术若要成为奥运项目,规则必须简化,易于操作”,以及在2003年出台了试验中的新规则(草案),“力争是武术竞赛规则更加科学,更符合奥林匹克运动的要求,为争取竞技武术进入奥运会创造条件”[8]44,就是很好的例证。
由于西方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尽管我们坚信中国武术具有体育的功能和价值,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坚持着中国武术的体育化发展,甚至是极力和全面地推进中国武术的体育发展之路。但中国武术在“体育”场域中的地位至今仍是尴尬和羞涩的。时至今日,这种将一切问题归结为中国武术“体育化”不充分的思维依然横亘在体育界。
3 中国武术在“体育”场域中发展的窘境
众所周知,对于世界文化的分类有多种方式,就文明而言,有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就文化的分类来看,我们常常会将世界分为东、西,也就产生了我们研究文化的两个立场,即: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文明、文化分类的理论,就形成了我们今天对体育的分类认同,即所谓的西方体育、东方体育抑或中华体育。但不论如何进行文明、文化、体育上的分类,其最为公理性的科学论断,就是这些文明、文化、体育之间的差异性是真实存在的。保持这种差异,并在一定意义上延续这种差异,应该成为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但非常荒唐的是,今天的中国武术在体育场域中的发展,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我们很难找到我们保护差异的行为和举动在哪里。
过去的一百年,求变求新早已成为中国武术发展的时代共识。融入体育,成为体育,似乎构成了中国武术发展的唯一出路。在西方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尺度面前,中国武术似乎总显得不够“体育”,似乎中国武术传统的问题正是导致它不能够“体育”的“原罪”。所以,导致了体育场域中的不同角色的人们———管理者、知识分子,甚至是武术人,在背负着中国武术体育化的事业压力下,将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去传统化”不够彻底的问题之上。进而导致了中国武术在“体育事业”中的地位异常艰难和尴尬。这种窘境,表现出的特征就如同《北京人在纽约》主题歌的歌词那样,“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并不在意”,“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而你却依然是你”。中国武术极度的体育化,并没有成就中国武术在体育事业中的地位。中国武术在中国体育中的地位,就如同中国画中的“补白”一样,始终难以成为中国画中核心的主题和素材。
作为竞技体育的中国武术,尽管今天也有了不同类型和级别的各种赛事,如: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亚运会、全运会等。但“非奥运会项目”的“美名”在体育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是根深蒂固的。“非奥运会项目”的“国家”地位,在今天的中国体育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2011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颁布《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所阐述的“以建设体育强国为奋斗目标,坚持以奥运战略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改革和完善举国体制”,“继续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为国争光”的目标追求,就不得不使我们再一次思考并产生对竞技武术在竞技体育之中命运的担忧。因为,对于“中国的‘举国体制’,可以想见,至少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内,还将是批不倒、骂不垮、攻不破的顽固堡垒”[9]。我们失去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武术进入的最好机会,也就决定了在未来的10年中,中国武术的“非奥运项目”的归类,仍不能退却和解套。这应该就是中国武术在中国体育发展中举步维艰的最大天敌。
作为唯一的一项至今仍存在于全运会之中的“非奥运项目”的中国武术,不仅在《奥运争光计划》中的地位是卑微的,而且在“非奥运项目”中的地位也是羞于启齿的。翻开最具影响力的年度“CCTV体坛风云人物”评选的历史记载,我们就会发现:“对于非奥运项目运动员奖而言,台球运动员拿过,国际象棋运动员拿过,登山运动员拿过,围棋运动员拿过……而作为国粹的中国武术,作为唯一存在于全运会之中的非奥运会项目却始终没有拿过,着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10]。甚至是在历届的评选中,武术运动员的入围也仅有2011年的一次。这次入围,还是在2011年广州亚运会中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首金的运动员,但非常遗憾的是亚运会的首金也没有给中国武术运动员带来福音。袁晓超的非奥运项目最佳运动员奖项的破灭,足以折射出中国武术的体育地位是那么的低微。因为,对于呵护、膜拜西方体育的“体育人”而言,中国武术的体育形态始终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和关注。
对于作为教育的中国武术而言,中国武术长期一直以来都是存在于体育课、体育专业、体育学下的。武术作为各级各类学校“体育课”中的一部分内容、一个项目,在学校体育考核核心主体为“大体育”的理念指导下,如今的学校武术课程早已被“虚化”。“有教学大纲,有教学内容、有教学计划,但无人教、无兴趣学,强化的武术教学指导纲要和弱化的武术教学实践形成强烈的反差”[11]151,“作为国粹的中华武术,在中小学的开展情况很不乐观。有70.3%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有些学校不仅没有增加学校武术内容,反而削减武术以增加跆拳道等域外武技项目”[12]。“名存实亡”早已成为各级各类学校武术教育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对于体育教育专业而言,武术本应成为其课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在长达4年的大学专业教育中,武术教学(普修课)内容的教学时数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108学时,变为今天的72学时。更有甚者,今天很多学校的武术课程,只有54学时、36学时。“淡化套路,强化意识,突出方法,强调应用”的体育教育专业武术课程改革指导思想,更是将武术推向工具理性的错误之举。
从“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武术硕士学位授予权,专门培养研究武术技术与理论的高层次人才,到1996年,国务院学位办通过论证投票,在上海体育学院设立了第一个武术理论与方法的博士学位授予点[11]143-145”,再到后来的体育学的四个二级学科的确立,武术学科的独立“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开始被“民族传统体育学”所替代。武术学科在“体育学”中的地位开始了弱化和动摇。更有甚者,在2010年教育部高等教育目录学科调整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存在意义开始受到质疑(教执委理论学科组宁波会议纪要)。很多学者认为,武术(抑或是民族传统体育)就是一个体育运动项目。关于它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可以归划在体育人文社会学中;关于它的教育训练学的研究,可以归划在体育教育训练学中;关于它的人体科学的研究,可以归划在运动人体科学中。尽管这次争辩,没有按照所谓的体育学者的意义,实现取缔“民族传统体育学”。但我们却不能不怀疑,“武术”甚至是“民族传统体育”,在一些体育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渺小和不屑一顾。中国武术在“体育学”中的地位摇摇欲坠。
就最具权威的由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国内一流专家编写的《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体育》[8]一书的内容来看,在32个图片彩页的近200余幅照片中,有关武术的图片也只有唯一的一张“北京2008武术比赛”;在厚重的416页60万字的文字记载中,对于中国武术30年的发展,几乎是无字描述,只在该书的第九章[8]344中用了175个字,对“北京2008年武术比赛”进行了专门的记载。中国武术的30年发展,就这本具有史学意义的“书”而言,唯其奥运模式的“北京2008武术比赛”,成就了武术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体育》中的存在。由此我们不能不说:中国武术的发展在“中国体育发展”中的地位、价值和作用,已经走到了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体育学者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忽略不计”的窘境中。
4 中国武术摆脱窘境的路径选择:从“体育”走向“文化”
回眸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武术发展,我们不能不说“体育”对中国武术的“桎梏”一直存在着。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我们唯一的模式几乎都是以‘西方’为中心,连自我批评、看待自己的唯一参照也是‘西方’”[13]的背景下。正是基于这种妩媚“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的心态存在,形成了在中国武术的发展问题上,同样出现了“我们所探讨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14]照搬西方体育理论与方法的盲目崇拜的现象。在我们谈论武术时,我们认可它的民族性,努力张扬它的中华性,但在选择其发展模式、路径、方法、手段时,我们却只站在“体育”的立场,只从“体育运动”出发。
摆脱这种不应存在的窘境,其核心的问题则在于我们是否可以树立并拥有一种“退”而求“进”的精神。将中国武术的发展问题,从“体育”领域,或者说“体育思维”中,“退“到“文化”领域和“文化思维”中来。这种“退”不是消极逃避,也不是对已有成果的否定和怀疑,而是应该从中华民族整个文化史、武术史的观点出发,重新思考中国武术的文化属性问题,重新探究中国武术的文化根底问题。
体育、西方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母体是西方文化,而中国武术的文化母体则是中华传统文化。近来文化界在思考文化发展的问题时,常常就“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命题进行广泛的思考和讨论。反观中国武术发展的问题研究,我们却一直在回避“我是谁”的原点研究问题,而一味地在“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上,仍选择“为了体育”、“依靠奥林匹克运动”作为目标,寻找着中国武术的发展路径、策略和对策。忽视对中国武术“我是谁”的理论探讨和甄别。“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决定着中国武术发展的命运,不仅在体育学界,甚至在武术学界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和不可逆转的公理。体育界的关于武术发展的“决定论”的意识泛滥,主宰着我们的选择和行动,也就导致了我们探究“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的武术发展目标的错乱。
英国有一句古谚语,“当你手中握有一把锤子时,什么问题看起来都像是钉子”。其实,我们对中国武术的体育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应验了这一古谚语的寓意。我们的中国武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地被“锤子”敲打,并在这样的敲打过程中异化为“钉子”,并行使着“钉子”的功能和价值。中国武术的当代改良和异化就是这样形成的。
中国武术的发展不能被“体育决定论”所左右,中国武术的发展更不能成为“体育”这把“锤子”下的一颗“钉子”,中国武术的发展问题应该按照文化发展的规律来选择发展道路。从“体育”走向“文化”的中国武术发展路径的选择,不是说中国武术不能够在“体育”环境中发展,而是强调中国武术不能只在“体育”环境中发展。改变只以体育作为武术发展资源的现状,拓展中国武术发展周围环境的空间,是未来中国武术发展的必然选择。因为,“文化特性由资源及周围环境的限制所决定,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15],这是文化生态学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总结。因为,中国武术“它以多个触角与哲学、军事、教育、医学、养生、竞技、娱乐、休闲、民俗等相关联,具有跨领域、跨学科、跨人群的性质,它不仅仅属于体育”。[16]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对文化的理解,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将这些文化意义最终凝结成一种符号[17]。就身体文化而言,“体育”应该是西方人在对西方社会文化意义的理解的基础上,形成了的具有鲜明特征的特定符号;而“中国武术”则是中华民族对中国社会文化意义的理解之后,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所以,“体育”、“中国武术”这两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的直接指向,从文化意义上而言,它不应该只是外显层的简单身体运动的相同,而更应该体现的是它深层所折射出的思想、精神、价值观念的差异和不同。也正是这些差异和不同思想、精神、价值观念的存在,才给予了这些符号存在的真正意义。拿体育作为标准来评价中国武术优劣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甚至是粗暴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中国武术在“体育”中的失语,在“文化”中的缺场,已经开始不约而同地汇成一股叠加合力与汹涌潮流,猛烈地冲击、拍打着中国武术文化防线和堤岸,形成国人对中国武术“我是谁”的质疑,导致中国武术的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并加重。
要捍卫中国武术的文化安全,必须着手实施和推进中国武术发展的中华文化思考,必须着手实施和推进中国武术从“体育”走向“文化”的步伐。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对已经在“体育”语境下形成的“新武术”的成就,展开文化意义上反思和考量;另一方面,则要我们重新从本土文化出发,寻找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武术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路径。中国武术发展的“文化回归”,就是要促成武术发展进程中“体育武术”向“文化武术”的转变。
因为,文化的保留和传承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连续过程,如果把复杂的历史文化问题用简单化线性思维来处理,只会引发更为复杂的问题。对于“中国武术”的当代改造,可以说我们就是选择了文化发展最为忌讳的“简单的线性思维”来处理的。只选择从文化的“外显层”入手来改良中国武术,并使其在同“西方体育”的交融时,极力强调它的“身体运动”特性,进而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中国武术发展走进了一个“去本求末”的发展阶段。
从“体育”走向“文化”的中国武术发展路径的选择,要求我们在发展中国武术时多一些“中国形象”的展示,在展示中国武术文化时多一些“中国身份”的凸显,在凸显中国武术时多一些“文化中国”的内涵。“体育”就是“体育”,它不可能替代“中国武术”;“中国武术”就是“中国武术”,它也绝对不可能变成“体育”。只有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中国武术的基本问题、发展问题,我们才能够很好地回答“我是谁”,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依靠谁”和“为了谁”的正确判断与选择。
中国武术要摆脱在体育场域中的生存窘境,越来越需要我们形成自己的理论论述和表达,而不是长期以来的“体育决定论”。因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环境所孕育出的文化产品,它们在组成方式、运动特征、思想理念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原本就是存在本质上差异的事物被生硬的“混搭”在一起,必然会导致问题的出现”[18],“清晰的道理却抵不过感情的痴迷,武术在体育系统中的形态自然是特别的扭曲”[2]305。摆脱“体育”的束缚,拓展“文化”的审视,才能够使我们对武术看得更加真实和透彻。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中国武术自身的发展立场,才能够找回中国武术在身体文化领域中的“话语权”。
5 结语
我们今天对武术“体育决定论”的批判,提出中国武术发展从“体育”走向“文化”的命题,并不是否定中国武术本身所具有的体育价值和功能,而恰恰相反地是在唤起我们对中国武术文化价值功能的挖掘和认知上的提升。中国武术是大文化,大文化需要大空间。匍匐在“体育”空间的中国武术,已经成为一个绻翼自囿的文化;只拿“体育”论述来评价中国武术,已经开始丢弃和异化我们的传统和根本。中国武术在“体育”空间中生存状态的持续,必然决定着它只是一只没有生命张力的蓬间燕雀。中国武术只拿“体育”作为论述和评价向度,也必然导致源远流长历史的隔断,文化特质的丧失。走进“文化”的中国武术发展,就是要努力建构和重构具有中国身份、彰显民族精神气概与民族主体性的中国武术文化体系,从而为建构和促成多元共生、和而不同、复调对话、互为主体的新的中国武术、世界体育新格局与新未来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杨文轩,陈琦.体育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2版):23.
[2]张洪潭.体育基本理论研究[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版).
[3]赵林.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第1版):3.
[4]丁祖豪.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1版):2.
[5]刘吉主编.新中国体育史优秀论文集[C].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7:68-77.
[6]王岗.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自尊[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30-39.
[7]邱丕相主编.中国武术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8]国家体育总局编.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体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9]杨早.话题2011[M].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206.
[10]王岗.中国武术当自强[J].搏击.武术科学,2010(2).
[11]邱丕相.中国武术文化散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2]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组编.上海:我国中小学武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
[13]王晖.面向新世界图景的文化自觉[J].文化纵横,2012(4):17.
[14]凡之.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打造自有品牌[N].光明日报,2012-04-20(第12版).
[15]王岗.武术发展的文化选择[J].体育文史,2001(3).
[16]卢元镇.中国武术竞技化的迷途与困境[J].搏击.武术科学,2010(3).
[17]姜飞.传播与文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第1版):29.
[18]王岗,吴松.中国武术发展的当代抉择:“求同”乎“求异”乎?[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2(2).